
□梁红焕
七月的风裹着丝丝雨水,把雨补的大山吹绿。车窗外,田埂上的玉米叶还挂着雨珠,远处的山峦像浸在翡翠里,连空气都带着股子甜润——那是刚被雨水洗过的草木香,混着泥土微微的腥气,吸一口,肺腑都像被熨帖过。

四五十分钟的车程,像是被山雾悄悄洇开的墨痕,等越野车碾过最后一段水泥路,雨补的村落已在视野里晃动。

等候多时的张书记,驾着他的私家车,熟门熟路地把车往山深处开,车轮碾过腐叶的沙沙声,像是在叩问山林的秘密。去年的菌窝子早被疯长的蕨类藏了起来,今年雨水太盛,草木都铆着劲地长,倒把寻菌的路变成了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,反倒添了几分野趣。

蹲在箐棵棵的落叶里寻找时,才懂“菌子看得见我,我看不见菌子”这话里的深意。它们太会藏了:牛肝菌把褐红的帽檐埋在松针下,只留半圈菌褶露在外面,像故意撩拨人的好奇心;鸡油菌更狡黠,乳白的身子贴着湿润的苔藓,不仔细看,倒像块落单的月光。手指轻轻捏住菌柄往上提的瞬间,总忍不住屏住呼吸——生怕稍一用力,就碰碎了这珍馐的梦。菌盖内侧还沾着新鲜的泥粒,菌褶里盛着没干的露水,凉丝丝的,像握着一小捧晨雾。


山路是跟着感觉走的。脚下的腐叶软绵绵的,踩上去像踩在云朵里,偶尔踢到石子,骨碌碌滚进草丛,惊起几只蹦跳的山雀。爱莲的父亲总走在最前头,八十岁的老人,头发银白却梳得整齐,蓝布衫的袖口卷着,露出结实的手腕。他眼尖,往往我们还在东张西望,他已弯下腰,从蕨类植物的缝隙里拈出一朵胖乎乎的菌子,“你看这品相!”声音洪亮得惊飞了枝头的蜻蜓。竹篮里的菌子渐渐多起来,有他拾的,也有我们偶然撞见的,凑在一起,勉强可以,菌香混着老人身上淡淡的烟草味,成了山间最特别的气息。


日头偏西时,山风里多了些凉意。低头看竹篮,近一公斤的菌子挤挤挨挨,有的菌盖边缘还沾着枯叶,像戴着俏皮的小帽。有人忽然叹道:“往后在市场见了卖菌的,可不能再还价了。”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心湖,漾开圈圈涟漪——那些凌晨三四点就摸黑进山的人,是踩着星光、踏着晨露,在湿滑的山路上跟时间赛跑,稍迟一步,菌子就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。这一篮鲜香里,原是浸着多少个披星戴月的清晨。


其实拾得到拾不到菌子都无所谓,关键是享受拾菌子的乐趣!你看那云雾漫过山脊时,像给青山系了条白纱巾;听那山涧的水叮咚作响,像是谁在石上弹着琴弦;连空气里浮动的草木香,都带着让人安心的暖意。就算竹篮空空,光是站在这山上,看阳光透过枝叶筛下金斑,看同行者弯腰寻菌时被汗浸湿的鬓角,看老人拾起菌子时眼里闪烁的光,就已是天大的乐趣了。

下山时,竹篮里的菌子在颠簸中轻轻碰撞,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在哼着不成调的歌。山风掀起衣角,带着菌子特有的清香,混着松针与泥土的气息,一路跟随着我们。忽然明白,这漫山寻找的过程,原是大自然最温柔的馈赠——它让我们慢下来,弯下腰,在与草木的对视里,在与泥土的亲近中,重新找回那份对微小美好的珍视。而那些藏在枯叶下的菌子,不过是山的信使,悄悄告诉我们:最动人的乐趣,从来都在脚下的路、眼前的景,和身边的人里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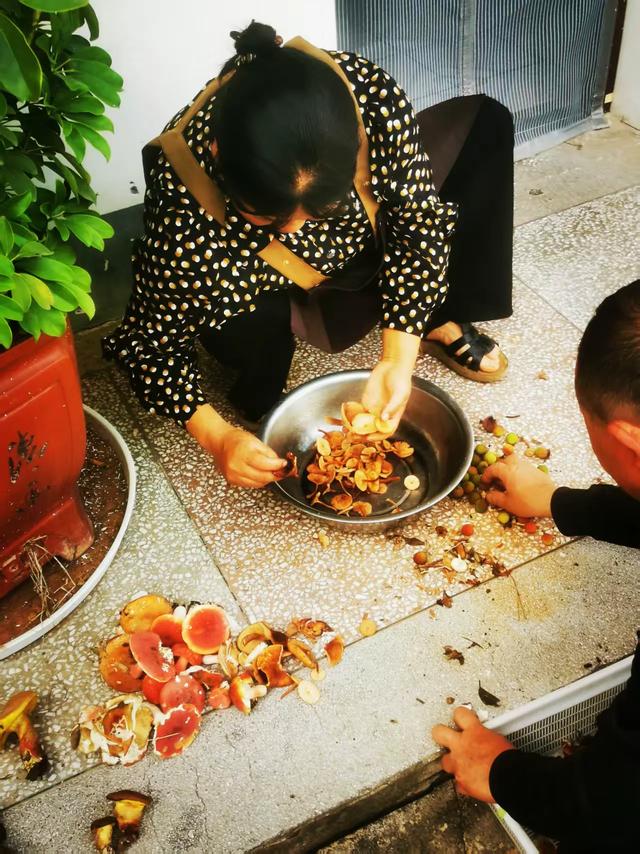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